徐望红教授:冠心病的四级预防
冠心病(CHD)的预防可采取四级预防策略,包括以政府通过制定政策,防止引起CHD危险因素出现的零级预防、“全人群策略”和“高危人群策略”并重的一级预防、以早诊断和早治疗为主要措施的二级预防以及以延长寿命、挽救劳动力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三级预防。
一、零级预防
零级预防是1978年由美国学者Strasser最初提出的一个预防医学概念,其理论基础是通过全人群健康干预,预防整个社会发生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而非等有了危险因素后再预防。
1982年WHO在其心血管疾病预防报告中介绍了“零级预防”的概念。2001年印度学者Rajendran进一步明确阐述了零级预防的概念。2010年,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提出心血管健康促进的“2020”战略目标,倡导通过心血管病的“零级预防”策略实现这一目标。2011年,AHA明确了零级预防与一级预防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阻止或尽量减少心血管病风险因素发生,防止其在一般人群中流行;而后者则是干预或改变个体及群体已经存在的心血管病风险因素,防止其引发心血管病及临床事件。零级预防比传统的三级预防更加提前,可以看成是预防工作的关口前移。
CHD的零级预防可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立法,限制CHD危险因素的产生和发展,预防不良后果的发生。例如,吸烟是导致CHD的危险因素,那么政府可通过实施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monitor)、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protect)、提供戒烟帮助(offer)、警示烟草危害(warn)、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enforce)并提高烟税(raise)六项有效的MPOWER控烟策略,尤其是颁布控烟条例,预防“吸烟”这一危险因素在人群中出现,从而降低CHD的风险,达到的“零级预防”的目的。
二、一级预防
CHD的一级预防是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针对危险因素而采取措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针对各种环境暴露因子所采取的消除病因的预防,也称病因学预防,如戒烟、调整饮食结构和加强体育锻炼等;另一方面针对高血压、脂代谢紊乱、肥胖、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失常所采取的药物干预措施,即发病学预防。前者通常采取“全人群策略”,对一般人群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让公众掌握心血管病的预防知识,提高对高血压、高胆固醇和高血糖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这是降低CHD发病最根本、最经济的手段。研究发现,90%的CHD可归因于吸烟、蔬菜水果摄入量少、运动少、酒精滥用等可变风险因素。后者则采用“高危人群策略”,对高危人群进行危险因素的重点管理,控制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对确诊的CHD患者进行个体化干预治疗,包括药物干预和行为干预。
三、二级预防
CHD的二级预防主要指CHD的早诊断和早治疗,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方面是采用临床常规的筛检、诊断和实施治疗方案,可称为临床学预防,如对于已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应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等药物预防再次心肌梗死的发生;第二是通过流行病学与临床结合,筛检高危人群,在高危人群中综合采取一、二级预防措施,可称之为综合性预防。收集并综合应用CHD的各种危险因素,可定量预测个体发病的绝对风险,并开发出可应用于防控实践的风险评估软件系统。目前许多国家已成功开发了相应的评估工具和软件系统,如美国Framingham评分系统、欧洲风险评分系统(EuroSCORE)、英国的QRSK2、ASSGIN Score和JBS3评分系统、新西兰的KnowYour Numbers评估工具等。我国也基于人群数据,开发出了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评估工具,预测个体未来10年的发病风险。此外,还可针对具有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糖尿病和吸烟等高危因素的人群开展早期筛查,识别动脉粥样硬化,采取有效措施如生活方式改善、药物综合治疗等进行干预,避免动脉硬化持续进展,有效减少心血管意外的发生。
四、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主要是临床医师对CHD各种并发症的积极治疗,防止CHD临床事件的再发生,达到延长寿命、挽救劳动力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一般来说,发生急性心血管事件的患者病情稳定后,可在二级医院进行短期康复或并发症的治疗,待进一步稳定后,可在社区医疗机构由家庭医生指导康复治疗和二级预防。
综上,CHD是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和生命的疾病。目前我国CHD防控形势严峻,不仅现患人数众多,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由于CHD的危险因素未得到有效控制,其发病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然而,CHD又是可防可治的。深入了解我国CHD的发病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政策和措施,控制CHD的危险因素,规范管理现患病例,提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水平,可有效降低CH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全人群策略”和“高危人群策略”,建立健全分级诊疗体系。这些举措将有利于降低我国CHD疾病负担,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陈伟伟,高润霖,刘力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概要[J].中国循环杂志,2017,32(6):521-530.
[2]CHEN G, LEVY D. Contributions of 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 to the epidemiology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JAMA Cardiol, 2016, 1 (7): 825-830.
[3]YANG X, LI J, HU D, et al. Predicting the 10-year risks of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China-PAR project (prediction for ASCVD risk in China) [J].Circulation, 2016, 134 (19): 1430-1440.
[4]曾哲淳,吴兆苏,陈伟伟,等.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中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风险模型研究与评估工具的开发[J].心肺血管病杂志,2016,35(1):1-5.
[5]HUAN T, ZHANG B, WANGZ, etalA systems biology framework identifies molecular underpinning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 2013, 33 (6): 1427-1434.
[6]JOEHANES R, YING S, HUAN T, et al.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ArteriosclerThrombVasc Biol, 2013, 33 (6): 1418-1426.
[7]Writing Group Members, MOZAFFARIAN D, BENJAMIN EJ, GO AS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6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Circulation, 2016, 133 (4): e38-e360.
[8]DEN HOED M, STRAWBRIDGE RJ, ALMGREN P, et al. GWAS-identified loci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e associated with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plaque presence at the carotid artery bulb[J]. Atherosclerosis, 2015, 239 (2): 304-310.
[9]KULLO IJ, JOUNI H, AUSTIN EE, et al. Incorporating a genetic risk score into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estimates: Effect on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s (the MI-GENES Clinical Trial) [J]. Circulation, 2016, 133 (12): 1181-1188.
[10]AL-ALLAF FA, ATHAR M, ABDULJALEEL Z, et al.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o identify novel genetic variants causative of autosomal dominant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Gene, 2015, 565 (1): 76-84.
[11]ARSENAULT BJ, RANA JS, LEMIEUX I, et al. Physical inactivity, abdominal obesity an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apparently healthy men and women[J]. Int J Obes (Lond), 2010, 34 (2): 340-347.
[12]XU WH, ZHANG XL, GAO YT, et al. Joint effect of cigarette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on mortality[J]. Prev Med, 2007, 45 (4): 313-319.
[13]BROOK RD, RAJAGOPALAN S, POPE CA 3rd, et al. Particulate matter air pollutio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 update to the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0, 121 (21): 2331-2378.
[14]ROSS R. Atherosclerosis—an inflammatory disease[J]. N Engl J Med. 1999,340(2):115-126.
[15]LIBBY P. Current concept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J].Circulation,2001,104(3):365-372.
知识来源
人卫知识数字服务体系
作者:徐望红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专家简介
徐望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主要关注肿瘤及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在人群中的流行特征、新的危险因素、防控策略、适宜干预技术及成本效果分析。曾参与多项大型国际合作课题的现场管理和实施,主持国内外研究项目10余项,主编参编著作5本,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
学术兼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因学分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分委会委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
荣誉奖励:入选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 评价此内容
- 我要打分
近期推荐
热门关键词
合作伙伴
Copyright g-medo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环球医学资讯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网络实名:环球医学:京ICP备08004413号-2
关于我们|
我们的服务|版权及责任声明|联系我们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京)-经营性-2017-0027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复核同意书 京卫计网审[2015]第034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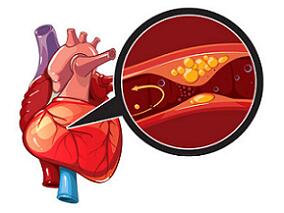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

